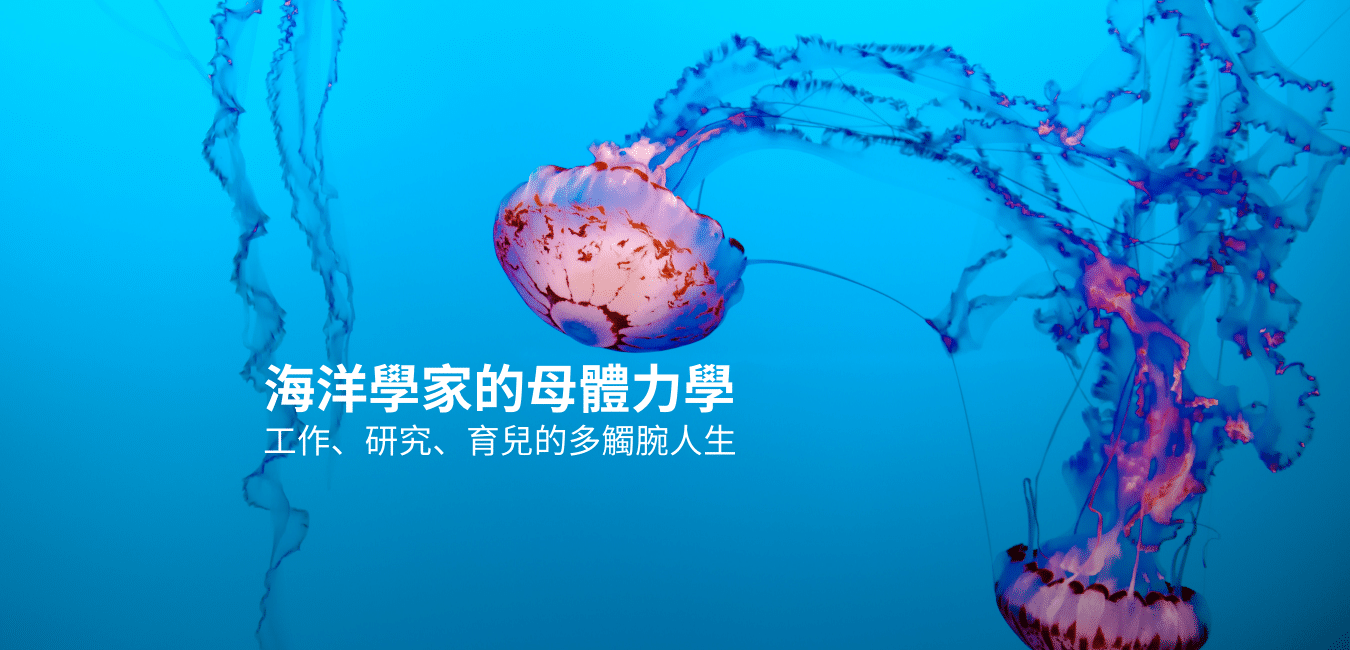林湛(Chan Lin)從小喜歡生物,大學聯考填到了中興昆蟲系。台大昆蟲碩士畢後,赴亞利桑那州大學的昆蟲科學中心取得博士學位(主修昆蟲科學,副修神經科學)。博士畢業後在馬里蘭大學巴爾的摩分校及史密森自然史博物館從事博士後研究,現職馬里蘭大學神經科學系專任講師
一般人如果想到聰明的動物,可能只會想到海豚猴子等哺乳類,很少會想到昆蟲蝦子。但是這些節肢動物不僅有大腦,很多種類還特化出可以處理複雜資訊的腦區,比一般人想像的厲害!
例如,人類的眼睛只能看到紅藍綠三種顏色,但螳螂蝦可以看到
12
種!他們的大腦和其他甲殼類相比沒有特別大,是如何處理
/
分辨這麼巨量的資訊呢?
又例如,人類的眼睛看不到偏振光的方向性,但是昆蟲蝦子可以,可以依此分辨東南西北,作為遷移的依據。這也是為什麼糞金龜推糞球的時候可以往同一個方向一直推,樺斑蝶、飛蝗、甲殼類也可以在沒有地標的環境中用偏振光來
“
導航
”
。
全世界有超過
80%
的動物是節肢動物,可以說是地球上演化最成功的一群。除了千奇百怪的生活史跟形態功能上的特化,他們大腦的可塑性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舉例來說,大部分的昆蟲是用腦中一對叫蕈狀體
(mushroom bodies)
的腦區記住味道還有其所連結的資訊。
但林湛的研究發現水生昆蟲的蕈狀體已轉而用來接受並處理視覺訊息!例如豉甲蟲
(whirligig beetles),
它有四個眼睛,在水表活動的時候兩個看上面,兩個看下面,隨時都是全視角!豉甲蟲的嗅覺已退化,不過蕈狀體不但沒有跟著退化,反而比其他昆蟲還發達,而且全部用來處理來自視覺區神經的訊息!
因為節肢動物的大腦蘊藏著各式各樣處理資訊的機密,許多研究經費反而是從軍方而來,期望發展人類儲存資訊和辨認方位的技術。

有趣的問題這麼多,但經費是那樣有限,期刊版面就那麼多。許多神經學的計畫經費主要是用於研究哺乳類、人腦,低等動物的腦特化研究不是主流。林湛每年平均投三個研究計畫,仍然常常在斷炊邊緣求機會。
博後的生活,是哪個老闆有經費哪裡去,家人也要跟著搬來搬去。林湛也曾經有去瑞典、德國研究的機會,但考量在美國用第二語言討生活已經不容易,如果去歐洲,不但大人要打掉重練,學習第三語言,連英語母語的小孩也要過上用第二語言的日子,重蹈父母移民的辛勞,於心不忍。
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的衝擊,在搬到馬里蘭州後變得鮮明。在亞利桑那州時,房租只要700, 但因著博後工作搬到物價在全美名列前茅的馬里蘭州,就變成了2000,整體空間還比之前小很多!博後的薪水在高物價州不過多個幾千塊,但物價卻漲了快三倍!想比之下,同期念光學系的同學,一畢業起薪就十萬起跳,還有各大企業搶著要,有時難免黯然傷神。
美國很多博士生是大學畢業直升,比台灣人大部分念完碩士當完兵才出國深究年輕很多,許多台灣人博士畢業已是三十好幾,不再是一人飽全家飽的單身漢。林湛在做博士後研究時還有兩個年幼的孩子嗷嗷待哺,博後的現實壓力不是靠PhD的頭銜光芒就能一筆勾消。
cover letter
,
personal statement, research statement,
教職的話還通常會要求
teaching statement
,以及最近很受重視的
diversity statement
,過去當助教還有自身曾經為國際學生的經驗就特別有幫助。
“
很上相
”
,留下最好的第一印象。
(gap junction)
可以關起來嗎?林湛老實的說不知道,然後說出根據自己的專業知識推測應該可以,接著下課就馬上查,下次告訴學生真的有研究發現可以,例如當一邊神經元死掉的時候,蛋白通道就會關閉停損。像這樣
“
考倒老師
“
的例子反而更能增進師生的互動,在面試時講那些經驗也很能引起評審委員的共鳴。
“
走路的人
“
書中所說的,每個人都在等機會,但你要在對的路上準備
;
如果你不在對的站牌等公車,你要搭的公車永遠不會來。同理,博後的時候不能只是埋頭把自己的東西做好,如果想找教職,就要先思考自己的教學理念,努力增加教學經驗,並好好準備
teaching statement, diversity statement
之類的申請文件。如果想找研究型職缺,就要有辦法拿到研究經費,同時拼發表,琢磨
research statement
,才能跟別人競爭。不能只是傻傻埋頭努力,方向要精準才對!
Monetary Bay
出海採集深海甲殼類。
20
年來的包容和不間斷的鼓勵。馬里蘭大學今年成立全新的跨領域神經科學系,在這波疫情的衝擊下,這個工作從申請到就職前後歷時將近一年,好在最後幸運地成為了他們在找的最後一塊拼圖
–
開授細胞與分子神經科學的專任講師。
182
個學生一起探索神經科學的起源與分子機制。這門課將來會一直開下去,林湛期許自己可以一直好好的把這份工作做好,也幫助學生走在他們想要的路上,走出屬於他們自己的路。

~如果喜歡我的分享,歡迎訂閱「海洋學家的母體力學」, 或按讚,追蹤,分享我的粉絲頁,我會很受鼓勵喔!~